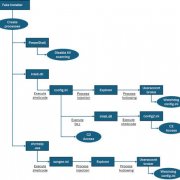媒體提供材料給思想,也塑造思想的方式
「大衛,停下來。停下來好嗎?停下來,大衛。你可以停下來嗎?」庫柏力克的電影《二○○一太空漫遊》片末一個著名又出奇深刻的場景裡,超級電腦HAL這樣祈求憤恨難平的太空人鮑曼。鮑曼差點被這台故障機器送葬在外太空,此時正平靜冷酷地拔除控制它人工頭腦的記憶迴路。「大衛,我的頭腦要消失了,」HAL無助地說著。「我可以感覺到。我可以感覺到。」
我也可以感覺到。過去幾年來我有股不舒服的感受,好像有人(或是有東西)在亂動我的頭腦,重整裡面的神經迴路,重編裡面的記憶。我的思考能力並沒有流失,最起碼我覺得不是這麼一回事;但是它有在改變。我不再用以前的方式來思考。當我在閱讀的時候,這種感覺最強烈。以從我很容易就能沉浸在書本或長文裡。我的頭腦會深入曲折的敘事或是彎蜒的論述,我也會一次花上數小時漫步在長篇散文中。這種情形現在已經不常遇到了。
現在,我在閱讀一兩頁後注意力就會開始飄移。我會坐立難安,忘掉先前的思緒,並開始找別的事情做。我覺得我一直在把我任性的頭腦拉回文本上。以前自然而來的深度閱讀,現在變成一種搏鬥。
我覺得我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十多年以來,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網路線上,到處瀏灠,有時還會在網路上碩大的資料庫中新增資料。身為一個作家,網路真是上天送下來的禮物。以前需要在圖書館書架中或期刊室裡費時數日的研究,現在只需要幾分鐘:用Google搜尋幾次、快速點了幾個超連結後,我就能找到所需的事實資料或名言錦句。我實在無法統計網路幫我省下的時間及汽油。我大部分的銀行交易和購物都是在線上進行的。我用電腦的瀏灠器來付帳單、約時間、訂機位和旅館房間、換發駕照,和發送邀請卡與問候卡。就算在工作外的時間,我很有可能在探索網路的資料叢林:讀寫電子郵件、快速掃過新聞頭條和網誌文章、追蹤Facebook狀態更新、看串流影片、下載音樂,或是單純在連結之間點來點去。
網路已經成為我的全能媒體,大部分從我雙眼雙耳進入腦內的資訊都是順著網路這個渠道流入的。這個異常豐富又容易搜索的資料收藏能供人立即取用,好處眾多;這些好處也已有許多人描述和稱讚。《考古》雜誌一名作家普林格寫:「Google是對人類的神奇恩賜,把原先四散世界各地、讓人無法從中獲益的資訊和想法採集、集中起來。」《連線》雜誌的湯普生觀察如下:「矽晶記憶的完整無瑕是對思想的恩賜。」
這些恩賜是真的,但是它們也有代價。一如麥克魯漢所提,媒體並不只是資訊的通道:它們為思想提供材料,但也塑造思想的方式。網路現在似乎在逐漸侵蝕我的集中和深思能力。不論我是否在線上,我的頭腦現在期望以網路散播資訊的方式來吸收資訊:像是一道快速流動的分子。從前我是茫茫字海裡的潛水伕;現在我像是騎著水上摩托車,在水面上飛馳。
也許我是個異類,一個局外人士,但事情看起來不像這樣。當我跟朋友提起我的閱讀困難時,許多人說他們也遭受一樣的痛苦。他們使用網路愈多,就愈需要掙扎才能專注在長篇寫作上。有些人擔心他們染上了慢性散漫浮躁症。曾任職於雜誌社、現在編寫關於線上媒體網誌的卡普承認他已經完全不再閱讀書本了。他寫道:「我在大學的時候主修文學,閱讀的胃口曾經很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猜測的答案是:「我現在所有的閱讀都在網路上,是否不是因為我閱讀的方式變了(也就是說,我只是圖個方便),而是因為我思考的方式變了?」
探討電腦在醫藥方面應用的部落客佛里曼也形容網際網路如何改變他的思考習慣。他說:「我現在幾乎完全失去閱讀、吸收篇幅稍長的文章的能力,不論是網路上的或紙本的都一樣。」這位任教於密西根大學醫學院的病理學家在電話上跟我繼續說明他的說法。他說,他的思考方式現在帶有如音樂「斷奏」的特質,這也反應他從許多網路來源快速掃過小段文章的行為。他承認:「我沒辦法讀《戰爭與和平》了,我已經失去這個能力了。就連一個超過三四段長的網誌文章也多到沒辦法吸收。我都只有大略瀏覽過去。」
經常在學術出版協會網誌上發表文章的康乃爾大學通訊科技博士班學生戴維斯,回憶起一段一九九○年代他示範網路瀏覽器給朋友看的舊事。他說,當那位女生停下來閱讀她瀏覽到的文章時,他覺得「震驚」,「甚至感到生氣。」他責罵她:「你不該細讀網頁的,去點有超連結的字就好了!」戴維斯現在寫道:「我讀得很多,或說我應該要讀得很多,但其實我沒有。我會略讀,我會快速捲動過去。我對長篇縝密的論證沒有耐心,雖然說我也會責怪他人過度簡化世界。」
卡普、佛里曼與戴維斯都是受過良好教育、有寫作長才的人;他們對於閱讀與集中能力退化似乎還不太悲觀。他們認為,他們使用網路得到的益處,包括快速取得成山的資訊、強大的搜尋與過濾工具、容易與少數興趣濃厚的讀者分享意見,整體說來可以彌補他們失去坐下來一頁頁閱讀書本或雜誌的能力。在一封電子郵件裡,佛里曼跟我說他「從未比最近更有創造力過」;他將之歸功於「我的網誌,以及我檢閱/略讀網路『大量』資訊的能力。」
卡普逐漸認為在線上閱讀許多互相聯結的簡短選段比起閱讀「兩百五十頁的書」來得有效率;不過他說:「我們目前還無法體認這種交互聯結思考模式的優越性,因為我們是以舊的直線思考模式來衡量它。」戴維斯則有如下的沉思:「網際網路也許讓我變成一個比較沒有耐心的讀者,但我想它也讓我在許多方面變得更聰明。我能接觸到更多文獻、文物和人,這表示有更多外來的因素會影響我的思考,進而影響我的寫作。」三個人都知道他們犧牲了一個重要的東西,但是都不願回到以前的樣子。
閱讀書本成為過時的觀念
對某些人來說,「閱讀書本」這個念頭已經過時,甚至還有點傻,就像是縫織自己穿的襯衫,或是自己屠宰動物來吃。「我不讀書了,」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前學生會長、二○○八年羅德獎學金得主之一的歐席這樣說。「我去Google就能快速吸收相關資訊。」當使用Google書籍搜尋功能就能在一兩分鐘內挑出重點段落時,主修哲學的歐席覺得實在沒有理由一章接著一章慢慢走下去。他說:「坐下來把一本書從頭到尾讀完沒有道理。這不是我善用時間的方法,因為我可以從網路上更快地取得所有我需要的資訊。」他認為,當一個人成為網路上的「高竿獵人」時,書本就顯得多餘無用。
歐席的情形看來不是特例,而是常態。二○○八年時,一個叫N世代的研究顧問公司發表一項網際網路對青少年影響的研究。該公司訪問了六千名他們稱為「網路世代」的人,亦即成長過程中一直使用網路的青少年。領導這項研究的研究員寫說:「沉浸在數位世界的生活甚至還影響他們吸收資訊的方式。他們在讀一頁文字的時候,不一定由左而右、右上而下。他們有可能跳來跳去,到處尋找他們感到興趣的資料。」有些人雖然不那麼在意非走在最前端不可,但仍然花大部分時間在線上,在桌上電腦、筆記型電腦或手機上打字。網路已成為他們工作、學校或社交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經常對三種生活層面都是必備的。還有些人每天只會上線幾次而已,到網路上看看電子郵件、追蹤新聞消息、研究他們感興趣的議題,或是上網購物。當然,還有很多人完全沒有用網路,可能是因為他們付不起,或是他們不想要用。無論如何,網路對整個社會而言已經明顯成為最多人選擇的通訊及資訊媒體,而且這和軟體設計師柏納李撰寫最早的網際網路程式碼僅二十年之遙。它的使用範圍空前地廣泛,即使以二十世紀大眾傳媒的標準來看都是如此。它的影響範圍也一樣遼闊。不論出於選擇或必要,我們已經接受網路獨有的高速搜集和散播資訊方式。
如麥克魯漢所預期,我們似乎已經來到一個知識和文化史上的關鍵點,兩種非常不同的思考方式要在此交替。我們為了取得網路的寶藏而換掉的(只有小氣的守財奴才看不到這些寶藏),正是卡普所稱「我們舊的直線思考模式」。冷靜、集中、不受干擾的直線思考頭腦被一種新的頭腦推到一邊,這種頭腦想要,也需要以簡短、不相連、經常重疊在一起的擊發方式來吸收和發布資訊,而且愈快愈好。曾是雜誌編輯和新聞教授、現在經營聯合線上廣告公司的巴泰爾這樣形容他在網頁中穿梭時,在知識方面感到的雀躍之情:「當我在幾小時的時間裡即時從多處取材堆砌出新物品時,我可以『感覺』到我頭腦被點亮,我『感覺』到我變得更聰明。」大部分人在上線的時候也曾有過類似的感受。這種感覺讓人陶醉其中,其醉人的程度使我們忽略了網路在認知方面造成的更深層影響。
重視文字的頭腦可能會消失
從古騰堡的印刷機使閱讀書本成為大眾活動起,直線、重文字的頭腦在過去五個世紀裡一直是藝術、科學和社會的中心。這種頭腦既柔軟又細膩,是文藝復興充滿想像的頭腦、啟蒙時代理性的頭腦、工業革命富有創造力的頭腦,甚至是現代主義滿是破壞顛覆的頭腦。不久後,它可能成為往日過時的頭腦。
超級電腦HAL 9000誕生(或是以HAL謙虛的說法,「開始操作」)的日期是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二日,問世的地點是伊利諾州厄巴納的一個神祕電腦廠。我在差不多剛好三十三年前出生,出生的地方是另一個美國中西部城市,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我的一生跟大部分屬於戰後嬰兒潮和X世代的人一樣,以一齣二幕戲的方式展開。這齣戲以類比青少年揭幕,道具快速全部替換後就進入數位成年階段。 當我憶起童年的景象時,它們看起來既安撫人心又陌生,像是從一部大衛林區執導的普遍級電影裡抽出來的定格畫面。這些景象裡有固定在我們?房牆上的肥大暗黃色電話,有著撥號用的轉盤和又長又捲的電話線;有我父親在調整電視上面像兔耳的天線,試圖讓擋住辛辛那提紅人隊比賽畫面的雜訊消失,卻徒勞無功;有躺在我們碎石車道上面捲成一綑、被露水沾濕的早報;有客廳裡的高傳真音響,在旁邊的地毯上散著一些黑膠唱片封套和防塵套(有些是我兄姊披頭四專輯的)。還有,在樓下充滿霉味的家庭共用地下房間裡,有著書架上面的書(很多很多書),以及它們五顏六色的書背,書背上寫著每本書的書名和作者。
一九七七年,也就是電影《星際大戰》上映、蘋果電腦公司成立那年,我前往新罕布夏州的達特茅斯學院就讀。在申請入學的時候我並不知情,不過達特茅斯學院當時早已是學術電子計算領域的頂尖學校,校方也在讓師生運用資料處理機器的能力上扮演關鍵的角色。校長克梅尼是位備受推崇的電腦科學家,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寫了《人類與電腦》一書,影響甚大。在此之前十年,他還是培基程式語言的發明人之一,這是第一個使用常用單字和日常語法的程式語言。校園正中央附近,在新喬治王朝風格、有著高聳鐘塔的貝克圖書館後方,蹲著只有一層樓高的基維特計算機中心;這是一棟看起來乏味、有些許未來感的水泥建築,裡面藏著學校的兩台奇異GE-635大型主機。這兩台主機跑的是劃時代的達特茅斯分時處理系統;這是一種早期的網路,能讓數十人同時使用電腦。分時處理系統就是我們今天個人電腦的雛型。如克梅尼在他書中所言,這使得「人與電腦之間一個真正的共生關係」得以存在。
我當時主修英語文學,為了避開數學和科學課程可說費盡心思;但是基維特中心位在校園的關鍵地帶,正好在宿舍和兄弟會集中地的中間,周末傍晚我常常會在公共電傳室裡的終端機前耗上一兩個小時,等著啤酒派對的氣氛炒熱起來。我通常會玩個大學部程式設計師(他們自稱「系程師」)拼湊出來的愚蠢原始多人遊戲,不過我確實也教會自己使用系統難用的文字處理程式,還學了一些基本的培基語言指令。
這些只不過是些數位小把戲而已。我每在基維特中心待一小時,大概也在鄰棟的貝克圖書館窩了二十多小時。我在圖書館深邃的自習室裡抱考前佛腳,在參考書架上的厚重書籍裡查資料,也在流通櫃台打工,幫忙處理借書及還書。不過,我在圖書館裡的時間大部分是在書架間的狹窄通道裡漫步度過。雖然有上萬本書圍繞,我不記得我當時會感到焦慮,不像現今所謂「資訊過載」出現的症狀。那些書的靜謐有一種安撫感;它們願意等上幾年,甚至是好幾十年,只待適合的讀者前來把它們從書架位置上拿下來。「慢慢來吧,」書本用灰啞的嗓音輕聲跟我說。「我們哪兒都不會去。」
到了一九八六年,我離開達特茅斯五年後,電腦才積極進入我的生活。在我太太感到無可奈何之下,我花了大約兩千美金(幾乎是我們全部的積蓄)買了一台蘋果電腦早期的麥金塔系列電腦:一台裝了最高配備的Mac Plus,有著一MB的隨機存取記憶體、一顆二十MB的硬碟,和一個小小的黑白螢幕。我還記得我拆開這台褐色小機器的包裝時有多麼興奮。我把它安置在我的書桌上,插上鍵盤和滑鼠,撥動電源開關。電腦亮了起來,響了一個歡迎的鈴聲,並一邊對著我微笑,一邊執行著讓它活起來的神祕過程。我深深被它吸引住了。
這台Mac Plus身兼家用電腦和公司商用電腦二職。我每天把它拖到我擔任編輯的管理顧問公司辦公室裡。我使用微軟的Word軟體來修改提案、報告和簡報,有時候也會打開Excel來輸對顧問報表的修正。每天晚上,我把它運送回家,在家裡用它來追蹤家庭收支、寫信、玩遊戲(還是很蠢的遊戲,但沒那麼原始);但最讓人分心的事情,是使用當時所有麥金塔電腦內附、創意十足的HyperCard程式來拼湊出簡單的資料庫。HyperCard是蘋果電腦創意數一數二的程式設計師艾金生所撰寫的,其使用的超文本系統預示了網際網路的模樣及感覺。雖然說在網路上點選的是頁面的連結,而HyperCard裡點選的是卡片上的按鈕,不過想法如出一轍,吸引力也一樣強。
電腦以細微但明顯的方式改變人類行為
我開始感覺到電腦不只是一個一步一口令的簡陋機器:電腦是一個會以細微但明顯的方式對人造成影響的機器。我電腦用得愈多,它對我工作方式的改變也愈大。剛開始的時候我沒辦法在螢幕上編輯任何東西。我會把文件印出來,用鉛筆做出修正,再把修正打回數位版本裡;之後會再印出來一次,再用鉛筆修改一次。有時候,我一天內會這樣來回十多次。但不知何時,我的編輯程序突然改變了。我發現我沒辦法在紙上書寫或修改任何東西。少了刪除按鍵、捲軸、剪下及貼上功能,和復原的指令,我就覺得失去了方向。我非得在電腦螢幕上做所有的編輯工作。在使用文字處理程式之中,我自己也變成了某種文字處理機器。
當我在一九九○年前後買了一台數據機後,更大的改變來了。在此之前,我的Mac Plus是台獨立作業的機器,功能僅限於我在硬碟上裝的軟體。當它和其他電腦透過數據機連線後,它開始有了新的身份和角色。它不再只是個高科技瑞士刀,而是一個通訊的媒體,一個搜尋、整理和分享資訊的裝置。我試用了所有的線上服務,包括CompuServe、Prodigy,甚至還有蘋果短命的eWorld服務;但是我決定長期使用的是美國線上的服務。我一開始訂購的美國線上服務只讓我一周上線五小時;我會細心地把珍貴的一分一秒分配好,好讓我能和一小群也有美國線上帳號的朋友通電子郵件,在幾個電子布告欄上追蹤消息,和閱讀轉載自報章雜誌的文章。事實上,我還喜歡上我數據機透過電話線與美國線上伺服器溝通的聲音。聽著那些「嗶」、「?」的雜音就像是聽兩個機器人之間的友善爭論。
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我身陷「升級輪迴」中,這讓我不太愉快。我在一九九四年讓年老的Mac Plus退役,換成一台麥金塔威力貓550,有著彩色螢幕、唯讀光碟機、一顆五百MB的硬碟,以及當時感覺快得出奇的33mHz處理器。我用的軟體大部分需要更新版本才能在新電腦上使用,它也能讓我跑各種不同、有著最新多媒體功能的新程式。我把所有新軟體安裝完後,我的硬碟也滿了。我必須再去買一台外接硬碟來擴充。我還新增了一台Zip高容量軟碟機,後來再增添一台燒錄器。過沒幾年,我又買了一台螢幕更大、處理器更快的新桌上型電腦,以及一台我在外出時能使用的攜帶型機種。在此同時,我的老闆禁用麥金塔電腦,改用使用視窗作業系統的電腦,所以我用了兩種不同的系統:工作時一種,在家時另一種。
大約在這個時候,我開始聽到有人談論一個叫網際網路的東西;據知情人士所說,這個神祕的「網路的網路」未來一定會「改變一切」。一九九四年《連線》雜誌的一篇文章宣稱我鐘愛的美國線上「突然過時」了。一個叫「圖像介面瀏覽器」的新發明許諾著一個更加精采萬分的數位體驗:「只要跟隨著連結(點一下,所連結的文件就會出現),你就能隨心所欲任遊線上世界。」這先激起我的好奇心,後來便讓我深深著迷。到了一九九五年末,我在工作用電腦上安裝了新的網景瀏覽器,用它來探索看似無窮盡的網路頁面。不久,我在家裡也有一個線上服務帳號,以及一台更快的數據機用來搭配這個服務。我取消了我的美國線上服務。
故事接下來的部分你一定知道,因為這八成也是你自己的故事:日益快速的晶片、日益快速的數據機、DVD和DVD燒錄器、容量以GB計算的硬碟、雅虎、亞馬遜、eBay、MP3、線上串流影片、寬頻網路、Napster和Google、黑莓機和iPod、無線網路、YouTube和維基百科、網誌和微網誌、智慧型手機、隨身碟、小筆電。這些有誰能抗拒呢?我可沒辦法。 (摘錄整理自第一章)
網路讓我們變笨?
數位科技正在改變我們的大腦、思考與閱讀行為
卡爾(Nicholas Carr)/著
王年愷/譯
貓頭鷹出版
售價:320元
作者簡介
卡爾(Nicholas Carr)
知名作家與思想家,專研商業策略、資訊科技及兩者的交叉點,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金融時報》《波士頓環球報》《華盛頓郵報》《大西洋月刊》《連線》《哈佛商業評論》《商業周刊》《富比士》《財星》等報章雜誌。著有暢銷書《IT有什麼明天?》(Does IT Matter?)與《大轉變》(The Big Switch),本書是他的最新著作,不僅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也入圍了二○一一年的普立茲獎非小說類作品決選名單。
熱門新聞
2026-02-06
2026-02-06
2026-02-06
2026-02-06
2026-02-09
2026-02-09
2026-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