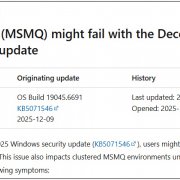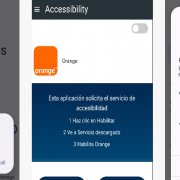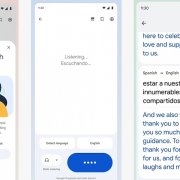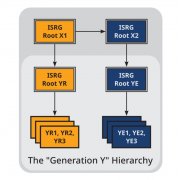假想你和另外三十五個人站在一起排隊,為了殺時間,排在你前面的那個人提議大家來打個賭。他拿出五十元美金,打賭這隊伍裡每一個人的生日都不一樣。你會和他對賭嗎?
或許你和大部分的人一樣,都不會和他對賭。現場只有三十六個人,但生日共有三百六十五個可能性,感覺上好像要賭贏的機會只有十分之一,所以你賭輸五十元美金的機率是十分之九。但實際上,你應該要和他對賭的,因為你贏得五十元美金的機率高於百分之八十。這個機率問題叫做「生日悖論,同時它也說明了涉及群體問題時的複雜性。
大多數人之所以會錯估這場賭局的賠率,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只要是情勢牽涉到很多人,一般人想到的都是自己而不是整個群體。如果提出賭局的那個人當時問的問題是,「這個隊伍裡有人和你生日是同一天的機率是多少?」那麼機率的確是只有十分之一左右,賭贏的機率的確很低。但是在一個群體之中,其他人與你的關係並不是唯一的變數。相反的,除了考慮隊伍裡的總人數外,你還需要計算各個人之間的關係。如果你把你的生日與另外一個人比較,只包含一組比較,那麼你賭贏的機率只有三百六十五分之一。但如果你把自己的生日和另外兩個人比較,好比是愛麗絲和鮑伯,再加上你。你可能以為機率是三百六十五分之二,但是你錯了。這裡牽涉到三組比較︰你和愛麗絲,你和鮑伯,還有愛麗絲和鮑伯的生日。如果是四個人的話,則是有六組比較,其中有一半的組別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如果是五個人的話,則是有十組比較。這樣一直往下算,算到三十六個人的時候,有超過六百組的生日比較。大家都以為一個群體中任意兩個人的生日是同一天的機率很低,但是他們忽略了如果是要計算「任意兩人」生日相同的比較組合就比一群人和你自己比較的組合數量多得多。這就是之所以會出現「生日悖論」的原因。
這個快速飆升的組合數量在任何事物的組合中都適用。如果你有一堆大理石,可能的組合數量也是用這相同的數學邏輯來計算。但是,在社會之中,這日益增長的複雜性就更棘手了。畢竟大理石不會有任何意見,但是人的意見可多了。當群體人數增多至中等大小時,要大家意見一致一開始只是有些困難,但是接下來就會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這樣的複雜度若是用物理學家安德森的話來說明,就是「數目一多了就是不一樣」。在一九七二年的《科學》雜誌中,安德森指出任何事物的聚集,不管是原子或是人,都顯現出無法以觀察其形成的成分來預測的複雜行為。當群體變大時,每個人不可能和其他人都直接互動。如果要維繫兩個人之間的關係是需要花費心力的,那麼當群體大到某種程度時,這樣的心力根本是無法持續一直做到的。布魯克斯在他的《人月神話》一書中提到類似的觀點,在進度落後的專案裡增加人手通常會讓專案進度更為落後,因為新進人員會增加群體協調的成本。因為這種限制一定會發生,也因為問題永遠無法徹底解決,只能加以管理,所以每一個規模大的群體都必須設法克服這種限制。現代人的基本解決方案就是把人集合在一起成為組織。
「組織」這個字同時代表了組織的行動以及從事組織行動的團體,我們會說「我們的組織組織了年度會議」。之所以用同一個詞來表示這兩件事,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說來,若是沒有組織就沒有辦法從事組織的行動。似乎要組織起來行動就必然要有組織來統合。典型的組織採行分層管理制度,基層員工對經理報告,經理再對更高層的經理報告,就如此層層上報。像這種分層管理的價值很顯然是為了簡化員工之間的溝通。
不管組織的目標為何,組織的運作自有其難度。它所承擔的每項交易,包括每一份合約、每一個同意事項、或是每一次會議,都要使用有限的時間、心力,或是金錢才能完成。因為有這些交易成本的產生,使用某些資源太過昂貴,只好棄而不用。也因此,沒有任何機構可以將它所有的資源全都投入它想完成的使命,機構還是須要投注相當心力維持組織的紀律和架構,才能繼續運作下去。管理交易費用所帶來的問題可以說是各種不同性質的機構一定會面臨的限制。
傳統管理架構之中,簡化協調步驟的能力可以幫我們回答一個在經濟學當中最著名的問題。那就是,如果市場這個機制這麼完美,我們為什麼還需要組織?為什麼我們不全在市場裡交易就好了?科斯在一九三七年首次在他著名的論文〈公司的本質〉之中提出這個問題。他也在該篇論文中首次有系統地解釋了組織分層制度的價值。科斯意識到在市場之中,勞動者只要和勞動需求者立約,就可以出賣他的勞力,同時也可以轉而購買其他人的勞力,這其中完全不需要任何經理人員監督。但是科斯解釋,一個勞動者全然自行交易的公開市場,會使得公司組織中的勞動力表現效益不彰,因為交易成本極高,特別是找出各種市場中現有選擇並與各方簽訂條約和履行條約的成本。
愈多人參與某一項任務,那麼不管要採取什麼行動,就會有更多潛在的協議必須達成,交易成本也會愈大,就和先前看電影的例子一樣。
管理耗費的成本,限制了集中控制的價值
一家公司只有在指導員工工作的成本低於所帶來的潛在收益時才會成功。大家很可能會以為要安排不同種類的群體合作,集中控制要比市場來得有效率。(的確,二十世紀時世界上大部分的政府都有此種假設。)但是此種指導性的管理有其限制,那就是管理本身所須耗費的成本。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哈克曼在《領導團隊》一書中研究了工作團隊的大小和效率。他在書裡說了一個關於非盈利機構董事長的故事,這個機構的董事會成員有四十人。有人問這個董事長這樣一個大型的董事會能做出什麼貢獻時,他回答,「一事無成」,而且他回話的語氣似乎是很滿意這樣的結果。由於管理所帶來的經常性費用,大型團體常常會原地踏步。只要交易成本在單一組織中貴到難以管理的地步時,市場的效率就比公司表現好(一般來說也比集中管理好)。
成本比公司和市場的潛在價值高的活動完全不會發生。這又是一個機構困境。因為組織的最小成本本來就比較高,某些活動可能有一些價值,但價值並未高到值得以組織的模式從事該活動。新的社交工具正在改變這個方程式,因為協調集體行動的成本變低了。最容易看見這種變化的地方,就是那些以傳統管理窒礙難行,但是以新的協調形式卻可行的活動。
後管理組織
當組織承擔起一項任務時,組織須要設法控制協調每個個體所發生的困難,當組織愈大時,此種需要愈迫切。最標準也最普遍的解決辦法是創造階層,而且把每個人依角色的不同安插進組織的不同層級之中。這種做法大幅減輕個體責任,並縮短溝通流程,使得再大的組織也得以管理。這樣的組織之中的個人必須同意接受管理,當然,通常是要付薪水給他們做為交換,同時也端看他們能不能做到主管的要求,才能持續收到薪水。
當指導新員工所須付出的成本低於管理成本時,組織才能從中獲利,並得以擴張。天主教教會和美國軍隊與任何營利機構一樣是有階級制度的,而其之所以需要分層的原因也大致相同。教宗和神父之間,或是總統和士兵之間的架構層級,都與紐約伊利鐵路公司中的負責人和隨車服務員之間的層級具有相同效力。這種分層的組織降低了交易成本,但無法完全去除交易成本。
想像一下一家有一千五百名員工的公司,每位經理有六名部屬。執行長有六位副總,每名副總帶領六名主管,再向下延伸。這樣的一家公司在基層員工和大老闆之間共有三層管理階層。如果你想要使基層員工更靠近大老闆,就必須增加每位經理所帶領的員工的數量。這樣做雖然可以減少管理的層級,但是也會減少直屬主管花在每一名下屬身上的平均管理時間(或是迫使每個人每天要花更多工時彼此溝通)。當組織變得非常龐大時,它就達到了科斯理論中隱含的限制。在某一個時間點,機構會到達再擴張的話就無法正常運作的地步,因為到時管理企業的成本會吃掉每一分利潤。這可以被稱為科斯天花板,再向上則任何一般機構形式都無法正常運作。
科斯理論也告訴我們在交易成本中做小小的改變所帶來的影響。當交易成本適度降低時,我們應該會觀察到兩件事。第一件事,最大型的公司會持續擴張。(換句話說,組織規模的上限與管理成本呈反向相關)。第二件事,小公司會更有效率,比起原先的高交易成本,現在能夠以更低的成本做更多生意。這兩個影響對戰後的工業世界而言也是極佳的詮釋。像七○年代的ITT和近年的奇異(譯注:或譯通用電氣)這樣龐大的企業集團,靠著他們在經營管理上的敏感度跨足了多元產業,只因為他們擅長管理交易成本。在此同時,中小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因為這樣的生意規模能更有效地發掘並掌握新契機。
但是如果交易成本不是適度地降低呢?如果交易成本徹底崩盤呢?從科斯原始的理論很難預測這種狀況,因為過去這種狀況只是純學術性的假設。但是現在這不只是學術理論,而是真正會發生,更精確地說,是已經發生了,而且我們已經開始看到結果。
只要在超過十二名員工的組織中工作過的人,都會了解機構中的制度成本。當你時時刻刻都有開不完的會,做不完的文書工作,或是凡事都得層層長官批示(都是麥卡倫惹的禍),就是在和制度成本打交道。一直以來,這樣的成本也只不過是大家在茶餘飯後閒聊時隨口抱怨的話題罷了。大家都在抱怨機構的經常性開支,對改變現狀也不抱任何希望。在那個世界裡(我們一直以來居住的那個世界,直到最近為止),如果想要擔當起任何重要的任務,那麼管理監督只不過是完成任務的一項必要成本。
那麼那些不值得花上半毛錢管理監督的工作會有什麼下場呢?當然我是指在之前的那個世界中,答案是「根本不會有開始,哪裡會有什麼下場可言」。
由於交易成本的原因,從未成為事實的商品和服務的名單可說是族繁不及備載。像收集業餘攝影者在倫敦地下鐵爆炸案中的影像紀錄這種事,若是在從前,根本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現在之所以留下了那些影像,是因為人其實都有與他人分享的慾望,防止我們與全世界分享的障礙已經去除。我們可以把這些活動想像成是位於科斯地板的下方,他們對某些人是有價值的,但是若以機構的形式去進行,則成本會高得驚人。因為一個機構有其無法擺脫的基本成本開銷,也使得那些活動完全沒有著手進行的價值。
群體合作的複雜性壓抑了合作慾望
人類與生俱來的群體合作的慾望和天分,每每在關鍵時刻就因為群體合作的複雜性被壓抑住。群體的協調、組織、甚至是溝通本就困難,而當群體擴張時又更是難上加難。也就是說任何幫助集體行動的方法都會傳播出去,不管這些方法是多麼沒有效率都強過什麼事也不做。小型的群體在協調行動時有幾種方法,像是一個個打電話給每名群體成員,或是建立一個電話聯繫網,但是大多數的方法就連在只有幾十個人的團體都不太管用,更何況是要協調數千人。對大規模的活動來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麥卡倫所提議的方法,也就是階層組織,分層管理。現今我們最普遍使用的機構體制只不過是在高交易成本的環境裡最不適合集體行動的爛方法中比較不糟糕的一個。
我們的新工具讓我們不須憑藉麥卡倫的策略就能組織起群體合作。與報紙相較,Flickr與攝影者的關係不同。報紙扮演了指揮攝影者的角色,Flickr則單純只是一個平臺,所有的居中協調都由使用者在網站上自行進行。這挺奇怪的。我們一般都認為機構比起未經協調的群體能完成更多事情,全都是因為機構有指揮員工的能力。但是在這些例子裡,居然發生了關係鬆散的群體比機構更有效率地完成了某些事。這都要多虧引進了使用者可以自行產生標籤的概念。現在僅憑攝影者個人的動機,不須要金錢報酬引誘,就可以收集到大量的照片。收集這些照片不僅沒有機構的介入,同時也是收集這些照片唯一可行的模式。
科斯的邏輯在這裡變得有些奇怪。交易成本的小幅下降使得生意更有效率,因為機構困境的限制沒那麼嚴重了。交易成本大幅下降則會創造出任何企業,甚或是任何機構都無法承擔的活動。因為不管進行某個活動變得多麼便宜,都不會有足夠的收益可以支付身為機構所必然會發生的各種費用。只要組織團體的費用門檻很高,那麼沒有管理成本的團體就會局限於負責小型的任務,好比晚上相約看看電影,舉辦露營之旅之類的任務。即便是客人們各帶一道菜的聚餐這麼簡單的事,也還是須要有主辦的家庭機構。既然現在以低成本進行大規模的協調已經成為可能,就出現了第二種類別︰不須機構的指揮就能進行的嚴肅且複雜的工作。協調鬆散的團體現在可以達成非機構體制無法達成的事,因為他們都藏身在科斯地板之下。
各種群體活動的成本,像是共享、合作、和集體行動,都快速下滑,先前隱藏在科斯地板之下的活動現在終於得見天日。我們以前之所以沒注意到那許多隱藏在地板下的事情是因為,在現在這個時代來臨之前,機構行動的替代方案通常就是不採取任何行動。社交工具提供了第三種選擇,那就是由組織鬆散的群體採取行動,在沒有管理監督的狀況下運作,同時也不以賺錢為目的。
從共享到合作到集體行動
過去幾百年中,大型機構的問題在於,不管是什麼任務,到底是由國家來統籌計畫才會獲得最好的成效,還是要透過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才會有好的成果。這場辯論是基於一個普遍但不能明說的假設,那就是人群是不會自行匯集在一起的。而且除了市場和統一管理以外,並無任何第三種選擇。現在我們有了選擇。我們的電子網路使得新奇的集體行動形式成為可能,也使得我們能創造出比以往更大也更發散的群體合作。非機構化的群體所能從事的工作範疇之大對現狀是一項極大的挑戰。
交易成本的崩解使人群可以更輕易地集合起來,實際上,由於它太過簡單,因此也改變了整個世界。這些成本的降低可說是當今革命性的演進,同時也是本書中所有內容的共有元素的驅動力。我們不習慣將「群體意識」視為一種獨立的類別,對我們來說,大學研討會和工會之間的差異性似乎比他們之間的相似性來得顯著。群體合作的表象看似是各自獨立,但是爆發的驅動力卻相同,那驅動力就是集會的簡易性。此種變化可以視為是一段長時間的過渡期,雖然表象不盡相同,但是卻在不同的場景下以不同的速度一一開展。這種過渡期基本上可以簡單描述為以下兩個問題的答案。為什麼集體行動大部分都只在正式組織中發生?又是什麼原因讓情況有了轉變?
現在我們有了通訊的工具,同時使用那些工具的社會模式,愈來愈適合我們與生俱來群體合作的慾望和天分。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能碰觸到科斯地板之下,我們能擁有像生日派對那樣的非正式群體,而且規模還是跨國性質的。我們目前所看見的泰國政變的業餘新聞報導、海嘯的記錄、還有無數個其他的例子,都是大家開始瘋狂實驗這些工具的初期成果。這些實驗的結果看起來不盡相同,當我們愈來愈擅長使用這些新工具時,結果會更分歧。近來集會的輕易性造成了影響力的擴散,而非收斂。而這些影響力依不同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緊密度而有所不同。
你可以把群體合作當成是通往活動成功的梯子,這些活動經由社交工具變為可能或是變得更好。梯子上的梯級按困難程度排序的話,依次是分享、合作、和集體行動。
分享對參與者所要求的門檻最低。很多像是Flickr這樣的分享平臺的運作模式是「用不用隨你,不用拉倒」。這樣的模式給予個人最大的參與自由度,也將群體生活所帶來的複雜性降到最低。雖然Flickr原始的設定是公開分享照片,但它也允許使用者選擇只將照片顯示給某些自行設定的使用者觀看,或是不開放給任何人看。在知情的狀況下與其他人分享你的作品是利用新社交工具最簡單的方法。(還有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分享作品的模式,好比Google讀取了上億網際網路使用者的連結。這些使用者一起建立了一種社群可取得的資源,就像是Flickr的使用者所做的分享。但是與Flickr不同的是,那些使用Google的使用者可不是主動選擇要貢獻自己的最愛連結給Google的。)
梯子的再往上一階是合作。合作比僅僅分享要來得難,因為這牽涉到改變你自己的行為以配合那些也正在改變他們的行為來配合你的人。和分享不同的是,分享只是一群參與者的群體而已,而合作則是創造了群體的身分認同,你知道自己在和誰合作。合作的一個很簡單的形式,也是社交工具裡普遍存在的形式,就是對談。人與人在一起時,即使是在網路虛擬的空間,都喜歡交談。有時候是用文字交談,像是電子郵件、即時通、或是簡訊,有時候則會使用其他的媒體,像是YouTube。
合作生產是比合作更複雜一些的形式,因為它會增加個體和群體目標之間的緊張關係。合作生產的試金石很簡單,就是沒有人能居功,而且若是沒有眾人的參與根本不會成功。從架構上來說,資訊分享和合作生產之間的最大差別在於,合作生產的過程中至少要做出一些集體決定。
在維基百科中特定題目的任何一個網頁都是經過眾人來來回回對話並不斷編輯才產生的(雖然日後還會持續修正)。合作不是一件絕對的好事,有許多工具要透過降低需要協調的工作量才得以運作,Flickr在彙總照片的過程中就是如此。合作生產可能有其價值,但是與分享相較,卻比較難成功,因為只要是和協調談判相關的任何事情,好比維基百科上的文章,就需要更多的精力才能產生結果。不像Flickr上的那些照片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愈聚愈多。(摘錄整理自第二章)
鄉民都來了--無組織的組織力量
克雷.薛基(Clay Shirky)/著;李宇美/譯
貓頭鷹出版
售價:350元
作者簡介
克雷.薛基
(Clay Shirky)
薛基針對網路世界對社會及經濟層面,特別是社會和科技網路重疊之處所帶來的影響,進行寫作、教課以及諮詢。目前於紐約大學互動電信專案計畫任教,並擔任諾基亞、寶鹼等企業的諮詢顧問。多年來,他的文章散見於《IEEE電腦雜誌》、《紐約時報》等。
熱門新聞
2025-12-12
2025-12-16
2025-12-17
2025-12-15
2025-12-15
2025-12-16